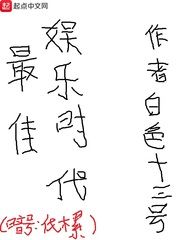员外府上,东跨院的院墙,塌了。
除了一片残砖,什么都没有剩下。
要说这院墙是如何被炸塌的?却要从那四个苦命的山贼说起,自从进了员外府的后园,他们就中了清风的鬼遮眼,在园子里四下乱撞,绕了不知多少圈子。白冉则趁此机会,在墙下埋好了火药球,又取了些火药粉末,洒在院墙周围作为引线。一切部署停当,白冉学了几声狗叫,给李伏报信。李伏念起了内急咒,逼着众人上厕所,叶秋带来的两个道姑,用起了鬼遮眼,引着众人去了公子房前,清风还是用鬼遮眼,引着四个山贼也到了公子房前,白冉抢先一步,也等在了公子房前,等到众人聚齐了,道姑们收了法术,这才上演了一场抓贼的好戏。可是清风至始至终没有收去法术,等卫兵赶来,又引着那伙山贼来到了院墙之下。
叶秋在东跨院里听到墙外一片嘈杂,知道计谋做成了,赶紧用隐身术摆脱了老夫人,临走之时又用定身法,定住了四个山贼。可怜那四个山贼动弹不得,只能站在墙下等死,适逢吕知府提着灯笼,站出来恐吓山贼,清风趁此良机,打掉了吕知府的灯笼,让那烛火正好烧在了火药粉上,火药粉哧哧啦啦一直烧到墙下,点燃了埋好的一串火药球,却把这堵院墙炸成了废墟。
王员外躺在地上,欲哭无泪,他却不知道老夫人就在东跨院的角落里,已然哭出了声音。
李伏冲到了众人之中,先拉起了白冉,又扶起了老员外,问道:『这到底是怎么了?刚才是什么声音?』
夏提刑自己站了起来,看着李伏笑道:『你还真是个好命的人。』
张校尉在旁道:『难道你命就不好么?要不是我拦着,你早就被炸成肉酱了。』
『瞧你那嘴脸!』夏提刑道,『我还用着你拦着?我早就看出这群贼人有诈!我只是想要留下一个活口,问一问他们的来意。』
张校尉冷笑道:『活口你是留不下了,都炸的稀烂,要问就去找阎王问吧。』
夏提刑道:『那却未必,这死人身上也有线索,』夏提刑转身对差人,道:『把他们尸体收了,带到府上好好查验。』
『慢着!』张校尉道,『这几个贼人身上带着火药,此事非同小可,我得把他们尸体带回军营,查一查这火药的来历。』
夏提刑道:『你要查火药的来历,且在周围捡些药渣便是,却要他们尸体作甚?』
张校尉道:『捡来药渣有什么用?天下的火药大同小异,他们身上肯定有装火药的器皿,让军中的匠人看一看,便能知道火药的出处。』
夏提刑冷笑道:『分明强词夺理!』
张校尉怒道:『老子说的就是理!』
吕知府在旁道:『二位不要争了,这几个贼人定是看上了员外的钱财,来此行凶作乱,既是在本府治下,理应由本府将尸体带回,示众三日,以儆效尤!』
夏提刑道:『刑狱之事,归我提刑司掌管,你怎可擅自僭越?』
吕知府道:『我乃城中百官之首,出了这等事情,怎能不给全城百姓一个交代?』
三人怒目相视,静默半响,夏提刑道:『这四个贼人是我提刑司的要犯,绝不容旁人插手!』
张校尉道:『明人不说暗话,这贼人是我手下军士制服的,你们谁也别想抢功!』
这张校尉确是说了一句实话,这三个人的确是想抢功,北山的草寇为害已久,谁也不想错过这大功一件。
眼看三人各不相让,徐员外在旁笑道:『几位大人何必相争?北山贼寇猖狂,今夜到雨陵城中行凶作乱,州府、提刑司会同骁骑营勠力同心,三军血战一夜,重创贼众,令贼望风丧胆,杀贼四十,力保一城太平!』
白冉在旁愕然道:『哪有四十人?分明只有四个,你这可是……』
徐员外瞪了白冉一眼,白冉抿了抿嘴道:『四十,是……四十……』
夏提刑看了白冉一眼,皱眉问道:『是四十么?恐怕不止吧?』
白冉不敢多说,徐员外赶忙道:『少了,少了,三位大人联手破贼,岂止四十,八十都不止。』
张校尉道:『不止,委实不止,到底杀了多少贼人,却得看吕知府怎说。』
夏提刑道:『刀剑上没有出力,笔头上的功夫可就看你了。』
吕知府一脸从容道:『好说,好说。』
白冉心下叹道:这撒谎吹牛的功夫,有时还真得甘拜下风。
事后,吕知府致书巡抚,言雨陵北山贼首马六,率众数百至城中洗劫,州府、骁骑营、提刑司三军并力,浴血奋战,大获全胜,毙敌二百一十四人,重创贼众!巡抚随即拟成奏折,报送京城,皇帝闻讯,龙颜大悦,重奖三人。杀了两百多个草寇倒也平常,然而兵部和吏部同心一力,这等情形却是少见,此事后来在朝中传为佳话,这都是后面的事情,表过不提。
当晚,三个人定下了计议,夏提刑还想查一查火药的来历,便在废墟之中寻找药渣,这一举动可是吓坏了王员外,要知道这堵墙里之前买了无数胎儿的尸体,捡到了药渣倒是不怕,若是捡到了骨头渣那可怎么得了。
『夏大人,不必找了,』王员外劝道,『王某素来嫉恶如仇,北山草寇恨我已久,此番来我府上行凶,既是意料之外,也算情理之中,全仗诸公之力,今晚却躲过了这场劫难,重生再造之恩,老朽铭感五内,没齿不忘。』
说完,王员外含着眼泪,便要下跪,众人赶紧上前扶起,吕知府道:『恩师这是作甚?却要折煞学生!』
夏提刑道:『惩奸除恶乃我辈本分,员外又何必客气?』
张校尉笑道:『好久无仗可打,正闲得膀子发麻,今晚可真是让我痛快了一回。』
众人纷纷上前劝慰,唯有白冉李伏一语不发,他们知道这老员外为什么哭,不是出于感激,而是因为心疼。絮絮叨叨说了半响,吕知府半天才想起了正经事,问白冉道:『公子怎么样了?』
白冉道:『诸公勿惊,公子有我徒弟保护,现在房中安睡。』
吕知府又问道:『除妖之事如何?』
白冉看着李伏,李伏笑道:『托诸公洪福,那妖邪已经粉身碎骨,灰飞烟灭。』
众人大喜,待去房中看过公子,公子已然醒了,气色却比昨夜更好。叶秋之前还在和夫人厮杀,而今已然坐在了公子身旁。
众人交口称赞,争相道贺,王员外当晚大排酒宴,以表感激。这次白冉没再客气,带上李伏和叶秋大吃大喝,大饱口福。席间,张校尉敬酒道:『白兄弟,之前是张某看错了你,别的不论,就看这身武艺,你也是个有真本事的人。』
『校尉大人谬赞,』白冉起身道,『若不是二位大人及时出手,白某今夜只怕已魂归地府。』
夏提刑闻言道:『白兄何时看见那般贼人,又如何与他们厮杀起来?』
白冉道:『白某听到门外有些脚步声,本以为是那妖邪来了,等出门一看,却见这几个人在院墙之下鬼鬼祟祟,我见他们各执兵刃,衣着怪异,待上前问了一句,这般贼人不由分说,便和白某打了起来。』
夏提刑皱眉道:『墙下?他们在墙下作甚?难道是想埋设火药么?我等一直都在后园,为何毫无察觉?』
『这个……』白冉不知该如何作答,却见张校尉一脸不悦,对夏提刑道:『你想审案是怎地?却不都说了,这事情交给吕知府处置便是。』
夏提刑起身举杯,赔礼道:『夏某就是这个怪癖,遇到事情总想问个究竟,白兄不要见怪。』
二人轮番劝杯,白冉招架不迭,连连推辞道:『在下有伤在身,委实不胜酒力。』
张校尉不悦道:『你有伤,我就没受伤么?都是些皮外小伤,有什么大不了,一会把我军医叫来,两下便能处置妥当。』
夏提刑笑道:『等校尉大人把军医叫来,拿着斧头和锯子,片刻便能收拾干净!』
张校尉怒道:『扯你娘的淡,哪个军医用斧头锯子看病?』
众人嬉闹说笑,唯有王员外面带愁容,吕知府在旁道:『今夜双喜临门,躲过一场浩劫,却又治好了公子,恩师为何不快?』
王员外举杯道:『子元莫怪,只因这般贼人凶悍,至今仍心有余悸。』
吕知府道:『恩师勿惊,但在吕某治下,那般贼人就是吃了虎胆,也不敢再踏进府中一步。』
直至夜深,酒宴散却,王员外命打扫客房,安排众人住宿,白冉哪还敢在这里久留,又说了一番真元耗损之类的借口,无论如何都要回山休养。吕知府、张校尉忙着商议请功的事情,却也推说公事繁忙,相继告辞,夏提刑想在府中再做些调查,却被王员外婉拒。临行之时,怕再有不测,三人各自留了些衙差和卫兵在府上把守。徐员外本打算在这住上一晚,可想起今夜发生的种种事情,仍觉心有余悸,却也连夜赶回了自家府中。
待众人走后,王员外来到东跨院,找见了夫人。夫人身上带着伤,披头散发,泪眼通红,只这一夜之间便憔悴的不成样子。夫妻两个抱头痛哭,哭过许久,夫人问道:『那般术士哪去了?今夜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!』
员外劝道:『那三个术士各有手段,单凭你一人之力,怎能敌得过他们?只要齐儿尚在,家业就在,待修好院墙,重新积累便是。』
夫人恨道:『难道就这么放他们走了?』
王员外道:『不急此一时,等这件事情的风声过了,再去报仇不迟。』
夫人平息良久,突然起身道:『不好!差点误了大事!得做个法术先把宅子里的鬼魂镇住,不能让他们去阴司告状!』
王员外道:『之前不说那群女鬼已经被剜了眼睛,毁了容貌,去不得阴司么?』
夫人摇头道:『女鬼不怕,只怕那些墙里的小鬼招来鬼差,到时候可就回天乏术了!』
夫妻两个赶紧去了正园,在一处的隐秘的房间里藏着夫人毕生打造的法器,可等进了房间,夫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,哭喊道:『没了,都没了。』
员外见房中空无一物,只觉五雷轰顶,上前低声问道:『法器,都没了?』
夫人哭道:『九十一件法器,一件不剩!这般畜生!定要将他们碎尸万段!』
夫人哀号不止,员外生怕被那般衙差听到,上前堵住了她的嘴,低声道:『莫怕,莫怕,且先找些工法简单的,打造两件应急。』
『工法简单,』夫人平静了下来,『工法最简单的,当属镇魂钉,可里边有几处细节,我忘却了。』
员外道:『你不一直留着祖师的秘笈么?』
『秘笈,秘笈!』员外夫人站起身来,却又跑到了另一间房里,翻找了半响,万念俱灰道:『秘笈,也被偷了。』
夫妻两个木然站在房间里,半响无语。
窗外渐渐响起了一阵哭声,似乎有人影在窗纸上晃动。
员外夫人拿出了身上仅存的两件法器,一个墨斗,一条铁锯,准备殊死一搏。